“在十四世纪后期欧亚大陆的政治环境下,朱元璋是个不折不扣的‘外来户’。他无法达到一个‘成吉思世界’(Chinggisid World)对君主身份的最基本要求:朱元璋的血管中连一滴黄金家族的血液都没有。他没有娶到一个黄金家族的女子,因之亦没有办法以驸马身份自居。哪怕是狐假虎威地替一位贵族政要发号施令,对朱元璋来说也是奢望。在大元的行政体系中,朱元璋无足轻重,从未扮演过任何政治角色。他的揭竿而起是对大元统治合法性的直接背叛。在相当长的时间段中,蒙古统治者及其散处欧亚大陆各地的拥趸对朱元璋的‘皇帝’身份都直截了当地予以否认和拒斥,即便在退居漠北以后,蒙古大汗亦选择无视朱元璋,根本不愿屈尊回复他的信件。以此,我们只有了然朱元璋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中无比边缘的位置时,才能够认识到他所提出诸项宣称时的魄力、勇气与创见。唯有在东部欧亚大陆政治文化的语境中,朱元璋处于元明之交的历史意义才能变得更加明晰。”
以上这段引文,是美国柯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亚洲研究暨历史学讲席教授鲁大维(David M. Robinson)在其近著In the Shadow of the Mongol Empire: Ming China and Eurasia(暂译名《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明代中国与欧亚世界》)结论部分的一段提炼。对于任何一位政治家而言,如何处理前任遗留的政治遗产总是对其政治智慧和手腕的极大考验,对于王朝的开创者而言更是如此。作为将世界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政治体亲手推翻而在其遗存之上建立新朝的“淮右布衣”,朱元璋面对蒙古帝国退场却未完全覆灭的情形下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究竟如何自处与应对,是一个让我们在设身处地的共情以后不免咂舌的历史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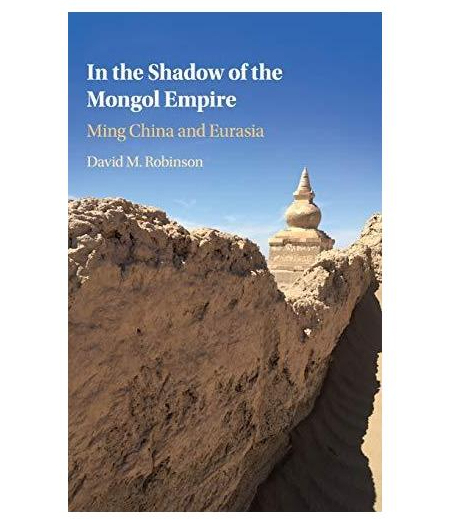
In the Shadow of the Mongol Empire: Ming China and Eurasia
2020年,鲁大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两本讨论元明过渡的重磅专著:Ming China and its Allies: Imperial Rule in Eurasia与In the Shadow of the Mongol Empire: Ming China and Eurasia。两本书中,前者已然以《称雄天下:早期明王朝与欧亚大陆盟友》的译名于2024年得以引介,并受到学界同仁关注,后者则因尚未出版译著的缘由,在中文学界所引起的相关学术讨论仍显不足。但事实上,这两本专著实为姐妹篇关系,学术聚焦一以贯之,且以《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为上篇。而据卜正民(Timothy Brook)透露,在投稿给剑桥大学出版社时,两书甚至本为一更大部头的作品。惟出版社从篇幅、出版和市场角度考虑,要求作者将之拆分为两本。因此,若不将两本专著并置阅读,可能便无法充分理解作者的学术关怀和野心。基于上述原因,笔者不揣浅陋,在曾经对《称雄天下》进行过述评以后,再试对《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的内容及其理论框架进行介绍与分析,以期推进中英文明史学界的学术对话,并由衷希望此书可以尽早翻译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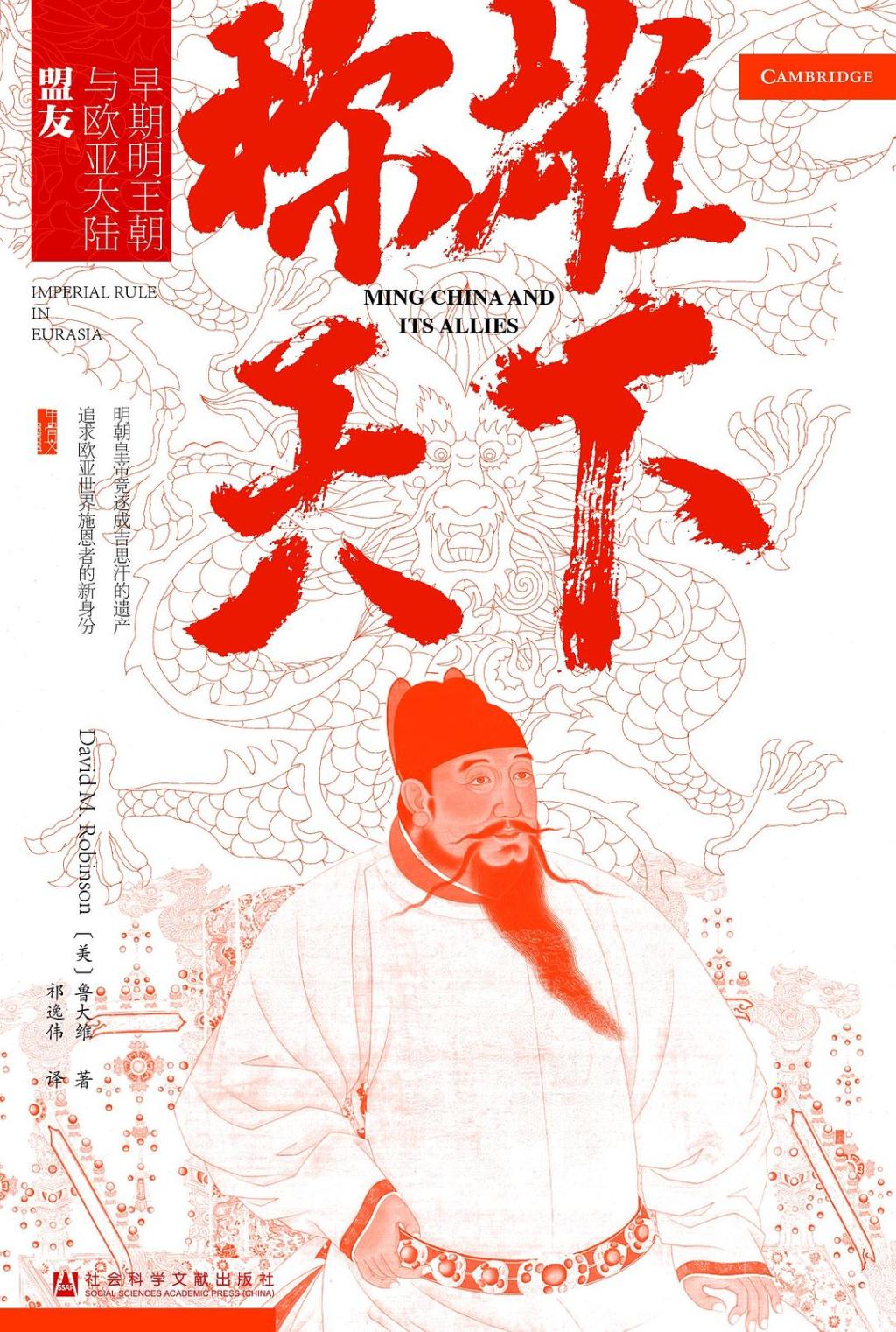
《称雄天下:早期明王朝与欧亚大陆盟友》( Ming China and its Allies: Imperial Rule in Eurasia)
在关乎中国历史朝代分期的理念中,唐以降的“宋元”往往被视作一个时空单元,而“明清”则另成一体。这样的思维惯性渊源有自,前者或与“宋夏辽金元”的错综纠葛不无关联,后者则和“清承明制”的习见表述脱不开干系。而与学者普遍承认唐宋之间存在变革、宋元之间表现出断裂以及不少学者所赞同的明清延续论不同,元明之间的朝代更迭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似乎仍是一个鼓励争鸣的开放场域。近年来,与汉族本位论调下对朱元璋民族革命意义的发覆有所不同,中英文学界多关注元明鼎革过程中的延续性。2003年,史乐民(Paul Jakov Smith)、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等学者围绕江南地区的历史演进态势提出了“宋元明过渡论”,约略同时期,李治安开始在北制、南制并存博弈的框架下讨论中国历史的长时段演进,并将元代与明前期视为北制因素强势的统合期。可以说,在强调蒙元时代对明初王朝的持续影响层面,《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是对上述中西方学术的一种延续。
在一个用以厘清概念和问题意识的导论及进行抽象提升的结论以外,《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依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十个章节。第一部分从蒙古人的视角出发,追溯了元明易代在欧亚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涟漪效应。在蒙古时代的欧亚大陆,人与物资的流动便捷而频繁。以此,即便在帝国崩解以后,大量蒙古人亦没有回到草原,而是成为新兴领地的实权阶层,并通过种种方式强化或者制造与旧帝国的关联以获得权威与合法性。在这个维度上,鲁大维将明朝放置在一个比较研究的框架下,因为各地统治者与朱元璋都需要面对同样的政治挑战,亦即如何处理后蒙古时代的权力继承问题——“北元”的统治者即为其中之一。在一种常见的历史叙事里,离开大都、退居漠北的元朝皇室所建立的政权被称为“北元”,且其运势衰微,在一连串的阴谋与杀戮之后,最终为鬼力赤篡位而舍弃了“大元”国号。但鲁大维提醒我们,关乎这段历史的文献材料相互间多有抵牾,明朝方面的记载、朝鲜方面的记录、各类实物遗存以及后世的蒙古史叙述之间往往存在矛盾,我们因之应当对任何一种习见的惯性思维保持审慎的态度。以此,本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鲁大维对文献的处理方式:一方面,虽然在还原“北元”历史的过程中对于明朝方面文献的使用不可避免,但鲁大维亦着力强调要对此类文献蕴含的汉地本位保有警醒,需尽力去除相关记载中的华夏偏见,也要看见“北元”政权其实从未放弃对于统治合法性的追求;另一方面,鲁大维用有限的文本记载和考古发现尝试还原了十四世纪晚期“北元”在黑水城的地方统治(第四章“Black City”)。明朝方面的文献选择性地淡化了一个事实,即蒙古势力在大都陷落以后仍对河西地区颇具影响。利用黑水城文书以及碑刻、印章等实物遗存,鲁大维细腻呈现了十四世纪晚期河西地区地方基层行政体系的调整、后勤补给的跨区域调拨以及以文书为载体的政令流通。既有研究多从明朝的角度讨论洪武时代河西地区行政区划的设置,尤其是在明代边略方针不断调整的语境中聚焦陕西行都司的形塑过程。而鲁大维的叙述则从“北元”视角出发,认为蒙古势力对河西持续的影响力或可帮助理解明代河西边政的嬗变。对有限的材料施以自洽的拆解和诠析,鲁大维的精妙叙述和深厚功力在这一章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鲁大维的文本细读能力在全书的第二、三、四部分中表现的更为典型。在这几部分中,鲁大维分别讨论了朱元璋向国内臣民(第二部分,第五、六章)及欧亚大陆其他政权(第三部分,第七至九章;第四部分,第十章)表达他理解元明鼎革的方式、逻辑和目的。为了概括“明廷如何讲述蒙古帝国的故事”(第3页),鲁大维提出了“成吉思叙述”(Chinggisid narrative)的概念,并以“叙述”一词所蕴含的“具有目的性的观点叙说”之意来提炼明初朝廷对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乃至整个蒙古帝国与时代的评述策略。与此同时,鲁大维尤其强调他对“明廷”(Ming court)、而非明朝社会、文化抑或政体的聚焦。这其实是鲁大维近年来一系列专著的共同关注,即其认为至少在明代前期,包括政治文化、宗教态度及外交逻辑的后蒙古时代的诸般要素其实都在“宫廷”的场域下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鲁大维看来,朱元璋时代的“成吉思叙述”绝非很多人认为的平面的、程式化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值得细细拆解的、能够反应洪武朝政治文化的文本凝聚(第五章)。通过在短时间内编纂《元史》,朱元璋希冀掌握对元朝历史的解释权,而各类文本中反复强调的“天革元运”之类的表述,则承袭自元代史书中针对宋、辽、金衰微状态而对“运”概念的调用,并起到了合法化他自己起事反元的功能。一方面,朱元璋在地理空间和政权权威层面着力凸显“北元”的边缘性,另一方面则适时的打“族群”牌,时而使用强烈的民族革命式的口吻,时而又转为对华夷一统的强调。而在第六章中,鲁大维更循着相同的逻辑,关注此一书写方式如何影响了明廷对元明战争的描写。
鲁大维对于明廷“成吉思叙述”的处理有两方面值得关注。首先,他对于明廷“成吉思叙述”的对象问题进行了考察。如情感态度激烈的“反蒙古”言论,显然是将国内臣民视作主要听众。而大元国运已失、明代元兴实属水到渠成的自然之选这样的逻辑,则主要是说给北元朝廷、尤其是身处明初疆域东南西北方向边地的那些摇摆者听的。与军事行动相比,这样的“宣传战”对于明朝开疆拓土、稳定边防而言同样重要。从史学方法的层面评说,鲁大维颇为关注文本的生产情境与生产目的,强调将特定历史文献放置在特定的时空架构中加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在通过《元史》尝试认识元朝时抱持谨慎,因为《元史》的编纂本身便是目的性极强的帝国工程,是明初王朝具有预设的、有意识的话语生产;其次,鲁大维对于史料的选择与判断亦值得击节。除却习见文献以外,他更广泛搜集材料,不仅使用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太祖皇帝钦录》及《明太祖御笔》,还深度参考了“无论在辑录的范围、编目的分类,皆远比《明太祖御制文集》优胜……其原始性及珍贵史料价值尤为突出”的《大明太祖皇帝御制集》,并在采录《天台林公辅先生文集》时尤其强调其使用的是静嘉堂文库本,从而避免了四库本可能存在的曲笔问题。由此可见,新一代的美国明史学家对于史料文献的掌握、使用及思辨能力已经与中文学界的研究者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了。
如果说《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的第二部分主要呈现的是明初“成吉思叙述”的国内版本,那么第三部分则凸显的是此一政治文化的外向输出。第七章《给大汗的信》考察了朱元璋在二十余年间向妥欢帖睦尔、爱猷识里达腊、脱古思帖木儿所发出的十余封信件。在这些信中,朱元璋不厌其烦的叙述了为何元运已失、为何他能够代元而立,以及为何这几位大汗应该接受甚至拥抱这样的变化。本章对这些信件的表述和逻辑进行了事无巨细的文本分析,聚焦信中关乎黄金家族命运与明朝政权合法性的劝服性甚至威吓性表达,并将之与同时期进行的军事行动及政治决策联系在一起,从而为看似重复和程式化的信件内容寻得了进行历史化诠释的空间。
第八章、第九章展示了朱元璋如何对环伺于新兴王朝的诸个后蒙古时代政权进行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的沟通、宣讲或拉拢。第八章是全然聚焦云南的一个个案,在某种意义上与“黑水城”章节的处理方式类似。在追溯了蒙古治下的云南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状态之后,本章着力描写了朱元璋在十四世纪七十及八十年代与云南的梁王、段氏及麓川等地方势力的沟通。在诸类敕书中,朱元璋选择说什么,选择不说什么,以及为何做出这些选择,都是他在充分了解云南地方的地缘政治结构以及几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以后的策略性选择。相较而言,第九章的关注人群则较为多元,包括了处于明朝疆域东北、北部、西北、西部和西南方向的故元势力及中亚的莫卧儿、帖木儿帝国两类政权。就前者而言,诸如王保保、纳哈出一类忠诚于元廷的军政实权派是朱元璋着力争取的对象,因为他们的表态不仅对辖下人众的归属颇为重要,更是其他同类型话事者掂量政治投资的重要参考。在与这一批区域实权派进行沟通时,朱元璋主要从负隅顽抗的徒劳、愚忠元廷的虚无以及对相关利益的承诺这三方面展开游说。至于莫卧儿、帖木儿帝国与明廷的互动,鲁大维广泛采录了中亚历史学家所整理的一手文献及相关学术研究,尝试还原了明初中国与广大西域地带的跨地域交往,并考察此类交往过程中的资讯流通及其之于地缘政治走向的意义。
值得说明的是,鲁大维在全书的第三部分(第七至九章)中对大量敕谕进行了全文英译,为日后学者的翻译工作与中英对读提供了重要参考素材。除此之外,鲁大维在分析具体文本内容时尤其注意明初朝廷对汉文与蒙古文、波斯文之间的翻译问题的处理。利用《华夷译语》中保存的多语种史料,鲁大维分析了华夏本位下的诸多概念,如天、天命、天运、气数及对元朝的各类贬低性表述是如何在相对应的非汉语文史料中进行对译转换的。限于篇幅,此一部分的讨论在书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然若诸位读者对此议题好奇,不妨参看现任教于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罗愚翰(Johannes Lotze)于2016年在曼彻斯特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帝国的译介:蒙元遗产,语言政策与明初的世界秩序,1368-1453》(Translation of Empire: Mongol Legacy,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Early Ming World Order, 1368-1453)。罗愚翰通过关注既有研究不甚瞩目的明初朝廷的“语言政策”,认为明初所接受的蒙元帝国的遗产并非仅见于制度设计或是领土扩张,在语言的层面亦有所体现。明廷有意识的模仿、并意图超越元朝,而多语言主义(multilingualism)则在象征层面和日常交流层面扮演了关键角色。明朝一方面继承了元代的政治文化实践方式,比如通过多语汇碑文来象征一个世界帝国无远弗届的权势,另一方面则将汉语提升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这与其在元代只是诸多官方用语之一的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此一过程中的张力需要新兴政权不断调适,知识、语言以及与之相伴的权力的转移,即为明初朝廷在接续蒙元帝国遗产过程中寻找平衡状态与自洽方式的切面。以此,罗愚翰博士论文与鲁大维的专书实存异曲同工之妙,即在军事、政治制度以外,主要从文化角度考察元明嬗变。
《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的第四部分只有一章,主要瞩目明廷之“成吉思叙述”对于朝鲜、日本、越南这三个“东边的邻居”的价值和意义(第十章“Eastern Neighbors”)。面对着对于蒙古时代体认不同、与蒙元皇室关系不同、与明初王朝互动方式不同的三个政权,明廷讲述“成吉思叙述”的方式亦需因地制宜。对于在相当程度上被并入蒙古帝国的朝鲜,朱元璋尝试利用半岛政治界与北元统治集团藕断丝连的联系,将其政治态度与“成吉思叙述”经由朝鲜转达给蒙古草原的潜在听众。对于并未受到蒙古势力过多浸染的日本,朱元璋则在相关敕谕中长篇累牍的对失败的“蒙古袭来”进行追溯,通过强调明朝武功较之蒙古大军更为强势的方式,希冀调用日本人关乎蒙古时代的历史记忆来迫使他们接纳明廷的权威与合法性。至于安南,因为在元朝统治期间多次发起的抗元斗争,朱元璋有意识的避免过度谈论“成吉思叙述”,而尝试寻求更为有效的沟通方式和语汇。
《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的结论部分对全书中的很多观察与观点进行了系统化的概述和提炼。鲁大维认为,朱元璋之所以面对各类听众不厌其烦的叙说蒙古帝国的崛起、荣耀与衰微,缘于这样的表述拥有广大的应用场域:明初的“成吉思叙述”不仅可以合法化朝廷对于权力的掌握、提醒人们元朝兴复的无望,还努力对那些尚持观望态度的豪强输出“附明即得生、附元即灭亡”的道理。蒙古时代是欧亚大陆诸多政权的“起点”,所以“成吉思叙述”是一种切合跨地域语境的、大家都能听懂的政治宣传。而这种叙述的底色则是“规劝”。在鲁大维看来,既有研究对于朱元璋与洪武朝的专制主义特质瞩目甚多,往往将其理解为杀伐决断的绝对权威,这当然是他尤为鲜明的一面;但与此同时,论者可能较少看到他反复调整语汇、用一种规劝式的口吻进行政治表达的面向。在这个维度下,朱元璋的“成吉思叙述”展示出的更多是耐心、容忍与坚持,并且贯穿了洪武朝始终——这直接指向了朱元璋颇为看重却无可奈何的一个要素,亦即本文开头所讨论的朱元璋在蒙元世界权力结构中极度缺乏的政治资本。
从朱元璋的不安、焦虑与政治因应说开去,鲁大维认为所谓的“成吉思叙述”其实尚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时空框架和历史逻辑。对于十五、十六世纪的明朝而言,大元的遗痕依旧在多种场域醒目而明显;帖木儿大帝去世以后,蒙古时代的遗产依旧统摄着帖木儿王朝的发展态势与地方实权派的行事逻辑,莫斯科公国、莫卧儿王国亦复如是。再至数百年后,我们依然能够在乌兹别克、准噶尔以及清王朝的政权底色中找到蒙古时代的影子(323页)。在这个逻辑中,《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元末明初的中国放在一个比较框架里进行审视。一方面,“感受前朝、讲述前朝”是无论任何政权都需要寻得自洽逻辑的政治需求,且对于与前朝之文化底色差异较大的政权而言尤是——无论是西班牙帝国对伊斯兰统治历史记忆的处理还是印度对于英帝国殖民痕迹的清理,我们都能够观察到前朝挥之不去的阴影并想象新朝的迫切与焦虑。另一方面,如果说某种讨论元明易代的旧范式是在民族国家线性史观中理解王朝变换的话,那么鲁大维此书便指出了此一政权更迭的全球语境——在十四世纪几乎可以被视作全球的欧亚大陆,对于蒙元帝国的政治文化遗产如何处理,是不分种族、宗教、文化的各地统治者共同思考的难题。《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聚焦于元末明初的数十年,切面不可谓大,然关怀亦不可谓小。
据笔者所知,鲁大维汉语极佳、韩语亦流利,这样的语文能力也形塑了他颇具全球性的学术目光:虽然以中国史家自居,但鲁大维没有就中国而论中国史,反而是广泛征引各种语文的史料文献,并尝试与多个领域的学术成果进行对话。鲁大维对中文学界学术前沿的跟踪亦提醒中国学者当对域外中国学研究保有及时的跟进,如此,方能在文明互鉴的逻辑下更好的叙说中国故事。
在为鲁大维的姐妹篇所撰写并发表于业内顶尖刊物《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书评中,卜正民对鲁大维之研究不吝赞美之辞,认为这两本书是“很多年未有的关乎中国王权统治的最有份量的研究”。卜正民认为,包括他在内的一代明史学者仍致力于观察明朝与世界的联系,尤其是借由晚明中国考察白银全球化将世界各地勾连在一起的形式。而新一代的明史学者则受到近年来学术范式的促动,更倾向于将元以降的中国放置在欧亚大陆的时空框架下进行考察。毫无疑问,鲁大维的一系列研究便是此一思潮转换的标志性成果。以此,我们不妨进而思考:如果明朝的前一百五十年尚在因应蒙古时代的影响,而后一个半世纪则与海洋世界发生了愈深愈广的联系,那么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理解这样的转变,又可以如何刺激我们去反思明代中国,反思这个朝代在元朝与清朝之间的位置,以及更广泛时空中的角色?更多的问题,亟待更多的研究去回答。
(本文原载于《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二十九辑“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汉籍与‘汉文化圈’专号”,此次媒体发表时标题为编者所拟,注释从略。)
